※本文摘錄「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一千一百哩太平洋屋脊步道尋回的人生」
火山口湖曾經是座山,馬札馬火山(Mount Mazama),是它的名字。它與我在俄勒岡州所經過的那一連串休火山--麥克洛克林山、三姐妹峰、華盛頓山、三指傑克山、傑弗遜山、胡德山等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比這些山脈還要更巨大,最高點的高度估計將近海拔一萬兩千英尺(約三六五八公尺)。馬札馬火山在大約七千七百年前噴發,造成災難性的巨大破壞,比一九八○年聖海倫火山(Mount St. Helens)的噴發大上四十二倍。這是喀斯喀特山脈一百萬年來最大型的爆炸性火山噴發。在馬札馬火山的災害後,火山灰與火山浮石隨之覆蓋周邊五十萬平方英里的大地,幾乎涵蓋整個俄勒岡區域,甚至遠及加拿大的艾伯塔省。

親眼目睹這場劇烈火山噴發的北美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克拉馬斯族(Klamath tribe),相信這場天災是冥府之神「勞」(Llao)和天空之神「史凱爾」(Skell)之間的一場激烈戰鬥。當大戰結束後,勞被趕回地府,而馬札馬火山變成一個中間空蕩蕩的碗狀地形。「火山口」--它被這麼稱呼著,有點像是一座隆起山脈的相反型態。一座心被挖空了的山。漸漸地,過了好幾百年,來自俄勒岡州的雨和融雪的水,開始聚積在火山口中,直到它變成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湖泊。火山口湖最深處超過一千九百英尺深(約五百七十九公尺),是全美國深度最深的湖泊,也是全世界最深的湖泊之一。
我對湖泊有些許的了解,畢竟,我是在明尼蘇達長大的;但當我步行離開愛許蘭時,依舊無法想像到了火山口湖時,看見的會是什麼樣的景象。我猜,可能就像是蘇必略湖吧,媽媽過世前的日子裡鄰近的那座湖,它那碧藍的湖水無窮無盡地往地平線那端綿延。旅遊導覽只說,當我第一眼看到火山口湖的外緣(比湖面高出九百英尺〔約二百七十四公尺〕)時,我會「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有一本新的旅遊導覽了。全新的指引聖經。《太平洋屋脊步道二部:俄勒岡州與華盛頓州》(Pacific Crest Trail, Volume II:Oregon and Washington)。我在愛許蘭的合作社裡整理行李時,將旅遊導覽後半的一百三十頁撕掉丟棄,因為我不需要敘述華盛頓州的部分。而在我離開愛許蘭後第一個晚上,在自己睡著前翻了翻這本書,跳著讀了一些片段,就像是當初我在太平洋屋脊步道的第一夜翻閱著有關加州路段的旅遊導覽。
從愛許蘭出發步行後,我一邊步行,間或可以在南邊的方向瞥見夏斯塔山的身影;但大部分時間,都走在樹林裡,看不見林外的景色。在背包客之間,俄勒岡州路段的太平洋屋脊步道常常被稱作「綠色通道」,因為它不像加州步道有著開闊視野。走在步道上,我不再有那種高高在上、俯瞰萬物的感受,不再能夠面對一望無際的景色,這讓我覺得有些不習慣。加州改變了我的眼界,但俄勒岡州又再一次地移轉了我的視角,讓它變得更貼近自我。步行在莊嚴宏偉的道格拉斯冷杉林裡,穿越枝葉繁茂的湖泊,通過有時會阻住去路的雜草與野薊。我穿過羅格河國家森林(Rogue River National Forest),走在巨大無比的古樹底下,然後來到伐木區,就像是我數週前所看到的那種。空曠的一片片空地,只剩下殘留的樹樁與樹根,暴露在這座濃密森林裡,此區的樹木已被伐木作業砍伐殆盡。我整個下午都迷失在這些殘跡之間,走上好幾個小時,最後終於踏上一條鋪設好的小路,讓它引我回到了太平洋屋脊步道上。
在這段路程中, 雖然陽光和煦、天空清澈, 溫度卻是微涼。在我通過天湖曠野區( S k y L a k e Wilderness)時,步道的海拔高度維持在六千英尺(約一八二九公尺)以上,隨著每一天的前進,氣溫降低得更加明顯了。當我沿著一道火山岩山脊往前走,廣闊的視野再次在我眼前展開,偶爾可以看見步道下方的湖泊,以及遠方綿延不絕的大地。儘管有陽光照射在身上,我仍覺得自己所感受到的天氣比較像是十月初的早晨,而非八月中的午後。我得不斷往前移動,來保持溫暖。只要停下來休息超過五分鐘,背上被汗水浸濕了的T恤就會變得冰冷難耐。從離開愛許蘭後,沒碰到過任何人,但此時,我遇見幾個一日步行客和過夜的背包客,他們各自從與太平洋屋脊步道交會的不同步道爬上來,往上方的山峰或底下的湖泊前進。大多數時候,我都是獨自一個人往前走,對我來說已習以為常,但是寒冷的天氣讓步道感覺起來更加空曠,疾風呼嘯,吹拂著那些堅忍不拔的樹木的枝葉。同時,走在步道上,感覺也更冷了,儘管我在這裡只偶爾看到幾塊小小的積雪,卻覺得這兒甚至比在塞拉城外的雪地裡還要冷。我意識到,這是因為當初這些山峰往夏季的時節推移著;如今,不過短短六週,卻已轉往離開夏季的時節前進,入秋季,步步緊逼,像是朝向將我往外推的方向擴散一樣。
一天晚上,我停下來紮營,把滿是汗水的衣服脫掉,穿上其他剩下的衣物,以最快的速度煮好晚餐。

一吃完東西,我馬上躲進帳棚裡,鑽進睡袋拉上拉鍊,只覺得寒氣刺骨,連閱讀都沒有力氣。我躺在睡袋裡,像個胎兒般蜷縮著身子,整夜都戴著帽子和手套,冷到幾乎無法入睡。當旭日終於升起,我看看溫度計--攝氏零下三度,帳棚外已覆蓋一層薄薄的雪。儘管我的水瓶整夜都在帳棚裡,就放在我身邊,但裡面的水結了冰。於是,我一口水都沒喝,開始拆卸帳棚,吃了一條蛋白質能量棒,取代我通常作為早餐的燕麥穀片加「勝過牛奶」豆漿粉。我又想起了媽媽。離開愛許蘭以後,她就不斷縈繞在我心頭,悄然而沉重,迴盪不去。此刻,在這個下雪天裡,我終於無法否定、無法忽視她的存在。
這一天是八月十八日,這一天是她的生日,她剛好滿五十歲了--如果她活下來的話。
她沒活下來。她沒辦法過五十歲的生日。她永遠不會滿五十歲--我走在陽光燦爛卻寒冷刺骨的八月天裡,一邊告訴自己。妳能不能滿五十歲,媽?可惡!妳能不能他媽的滿五十歲?我往前走,一邊想著,心中的憤怒愈來愈強烈。我無法相信自己竟然那麼生媽的氣,氣她不曾活到她五十歲生日這一天。我心中升起一股想要一拳打在她臉上的衝動。
她前幾次的生日並沒有帶給我這種狂怒感。在過去幾年裡,我只是覺得悲傷。第一個沒有她的生日到來時(若她還在的話,是四十六歲),我與艾迪、凱倫、雷夫、保羅一起,將她的骨灰鋪灑在花壇之中,那是我們親手為她做的,在我們的土地上找了塊空地,用石頭圍出了一個小小的花圃。她死後的第三個生日,我只是靜靜地坐著哭泣,聆聽茱蒂.柯林斯(Judy Collins)的專輯《日之彩》(Colors of the Day),流洩出每一個音符都像是我自己身上的細胞。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媽時常播放這張專輯,它承載了太多與媽媽相關的回憶。每一年拿出來聽一次,就是我能夠忍受的極限。這些歌曲讓我感覺媽好像就在這兒,在我身邊,與我一起站在這個房間裡。但她並不在,而且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我連一句歌詞都沒辦法承受。我把腦中那個混音電台裡播放的每一首歌都刪除得乾乾淨淨,絕望而慌亂地按著那個想像中的倒轉按鍵不放,強迫自己的大腦靜止不動。這一天是我媽到不了五十歲的生日。這一天,任何歌曲都不准出現。我越過高山湖泊、行經方塊狀的火山岩石,夜晚的冰雪融在耐寒的野花上,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走,腦中刻薄無情地想著關於媽的種種。四十五歲過世是她做過最糟糕的一件錯事。我一邊走著,一邊在心裡舉出她其他做錯的事情,仔細地將它們列成一張表。
一、她曾有一段時期,每隔一陣子就會吸食大麻,而且毫無顧忌地在我們姐弟面前這麼做。有一次,她吸完大麻以後,飄飄然地說:「這只是一種藥草。就像花草茶一樣的意思。」
二、當我們住在那棟滿是單親媽媽的集合式公寓裡時,弟弟、姐姐和我時常被單獨留在家裡。她說我們已經夠大了,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幾個小時,因為她沒有錢請保母。還有,她說如果發生什麼事,我們可以向公寓裡其他的媽媽求救--但我們需要的是我們的媽媽。
三、在這段相同的時期裡,當她抓狂生氣的時候,常常威脅要用木湯匙揍我們,而且有幾次她真的這麼做了。
四、有一次,她說如果我們想要用她的名字稱呼她,而非叫她「媽媽」,她完全不介意。
五、她有時會冷淡、疏遠她的朋友。她很愛他們,但她總是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我覺得她從未對任何朋友完全敞開心房。她堅持著「血濃於水」的信念,儘管我們家其實親緣淡薄,親戚幾乎都住在離我們幾百英里遠的地方。她保有一種孤立、封閉的態度,雖然參與朋友的社交圈,卻不讓她的家庭有任何程度的涉入。這就是她過世時沒有人挺身而出的緣故吧。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朋友會扔下我,讓我一個人在無法避免的哀慟中流亡。因為她從未張開雙臂、緊緊將他們擁入懷中,所以他們也沒有伸手擁抱我。媽死後,他們祝我平安順利,並未邀我去吃一頓感恩節晚餐,也不曾在她生日當天撥電話給我,打聲招呼。
六、她樂觀到令人惱火的地步,老是說一些蠢話,像是:「我們並不窮;我們有滿滿的愛,所以我們很富有。」或是:「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必定幫你開啟另一扇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這些話總是讓我想要跳起身來,掐住她的脖子。即使在當初她快死的時候,她也依舊短暫而淒涼地顯露出她樂天的個性,相信只要她喝掉一大堆養生小麥草汁,她就不會死。
七、我高三時,她從來沒有問過我想去哪裡念大學,也沒有帶我去大學參訪。在入學前,我甚至根本不曉得有「大學參訪」這件事;是其他同學告訴我有關他們參訪之旅,我才知道的。她就這樣讓我自己摸索,讓我傻傻地申請了聖保羅的一所大學,單純只因為它在介紹手冊上看起來很不錯,距離家裡只要三小時車程。我承認,高中時我確實不是什麼用功的好學生。我成天扮演著漂亮無腦的金髮傻妞的角色,以免自己被欺負排擠--畢竟,我家住在需要拿蜂蜜桶充當馬桶、在爐子燒柴火取暖的房子裡;我的繼父蓄著長髮和蓬亂的大鬍子,整天開著他的皮卡小貨車到處跑(那是他用噴燈、鏈鋸、幾塊二乘以四英寸窄木條,將一輛報廢轎車改裝而成的);而媽總是不除腋毛,還會對那些血氣方剛、愛好槍械的本地人說出類似「說真的,我覺得打獵和謀殺沒兩樣」的話。雖然我裝出傻呼呼的模樣,但媽知道,私底下的我是聰明的。她知道我對於知識是多麼熱中,每天不斷地啃著書本。我在考過的標準化測驗(standardized test)裡每一項都拿到很好的成績,嚇了大家一大跳,只有媽和我自己一點都不訝異。當時她為什麼不對我說:嘿,或許妳該申請哈佛?或許妳該申請耶魯?在那個時候,哈佛和耶魯根本不曾出現在我的腦海裡。它們感覺上完全是虛構的傳奇學院,好像只有在小說裡才會讀到一樣。一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哈佛和耶魯是真實存在的,而儘管它們根本不可能接受我的入學申請--我是真的沒有達到它們的標準,但我媽連問都沒有問過我是否想要試試看,還是令我感到心碎。
我知道,現在已然太遲了。只能怪罪我那個不在人世、孤立、過度樂觀、不曾替我念大學做準備、偶爾拋棄小孩、吸大麻、揮舞木湯匙、歡迎我們直呼她的名字的母親。她不及格。她是那麼徹底讓我失望。
去她的。我心想,心中升起了一股狂怒,停下了腳步。
然後,我放聲哭嚎。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我只發出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嘶吼,用盡全身的力氣,讓我甚至連站都站不穩。我彎下腰痛哭失聲,雙手環抱著膝蓋,背包沉重地壓在我的背上,雪杖「噹」的一聲落在我身後的泥土地上。我就這樣悲泣著我那該死的愚蠢人生。
它完全錯了。它殘酷無情地將媽從我身邊奪走。我甚至無法好好恨她。沒辦法擁有正常的人生經歷:從嬰孩長成青少年、開始疏遠她、跟朋友一起說她的壞話、為了那些我認為做錯了的事情質問她。隨著年歲漸長,我開始了解到她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發現她已經做得很不錯了,然後,終於再度張開雙手親近她。她的死毀了這一切。毀了我。在我最年少無知、滿懷傲慢的時刻,它將我的成長之路一刀截斷,逼得我必須立即跳到大人階段,原諒她作為母親所犯下的所有過失,同時又迫使我永遠都像個孩子一樣長不大。那個太不成熟的時機,既是我人生的終結,也是我人生的起點。她是我的母親,但我已沒有母親。我獨自一個人被她困在原地,然而困住我的她甚至不在身邊。她將永遠是那空蕩蕩的碗,沒有人能填補。我得自己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填滿它。
去她的。我一邊低吟著,一邊繼續向前走了幾英里,步伐因憤怒而加快。但過了不久,我就慢下腳步,然後在一塊大岩石上坐了下來。一叢低矮的花朵生長在我腳邊,它們淺淡粉紅色的花瓣圍繞在石頭的邊緣。番紅花。我心想。這個名字立刻浮現在腦海中,因為媽曾經告訴過我。在我鋪灑她的骨灰的泥土上,就長滿了這種花。我伸出手,輕輕碰了碰其中一朵花的花瓣,感覺我的憤怒逐漸從我體內流洩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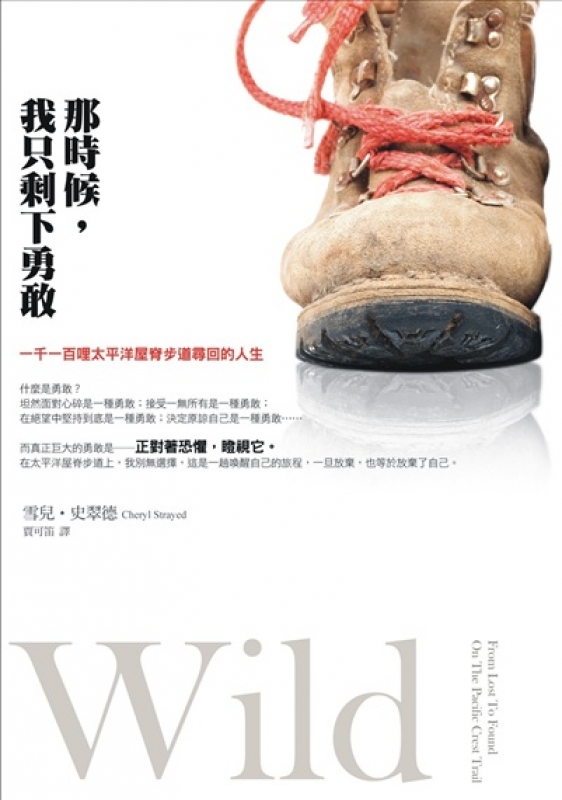
書籍相關資訊
- 書名: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一千一百哩太平洋屋脊步道尋回的人生
- 作者:雪兒•史翠德(Cheryl Strayed)
- 出版社:臉譜出版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29日
